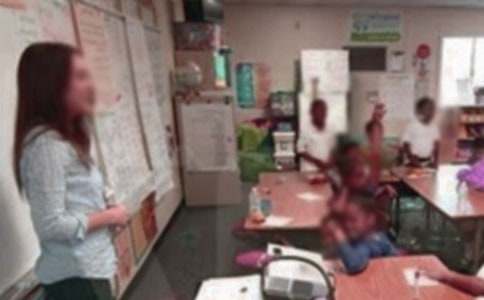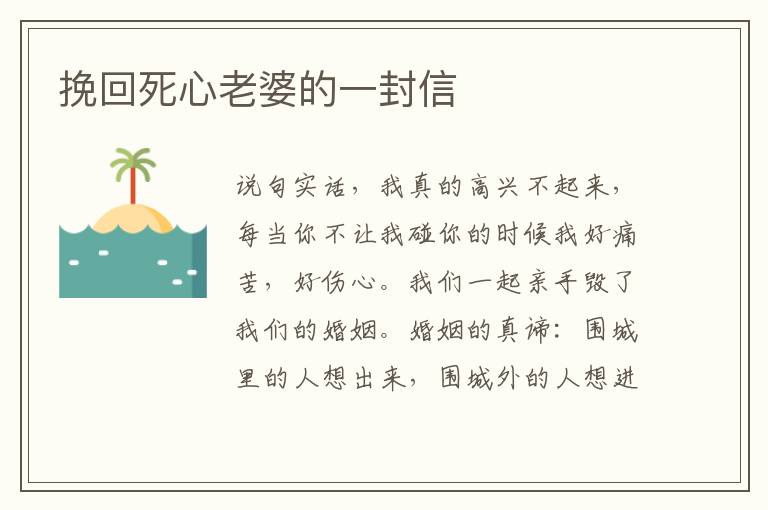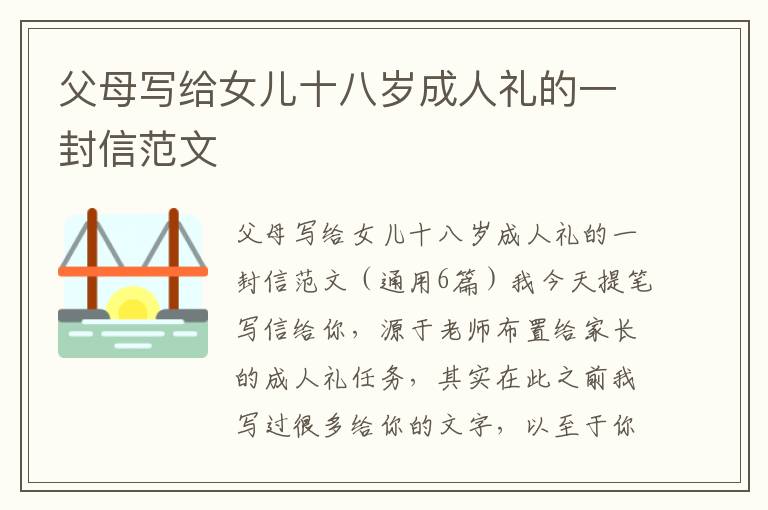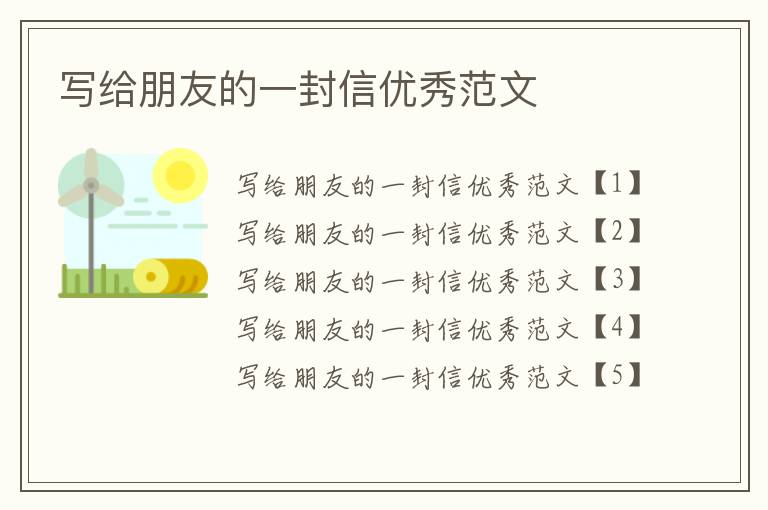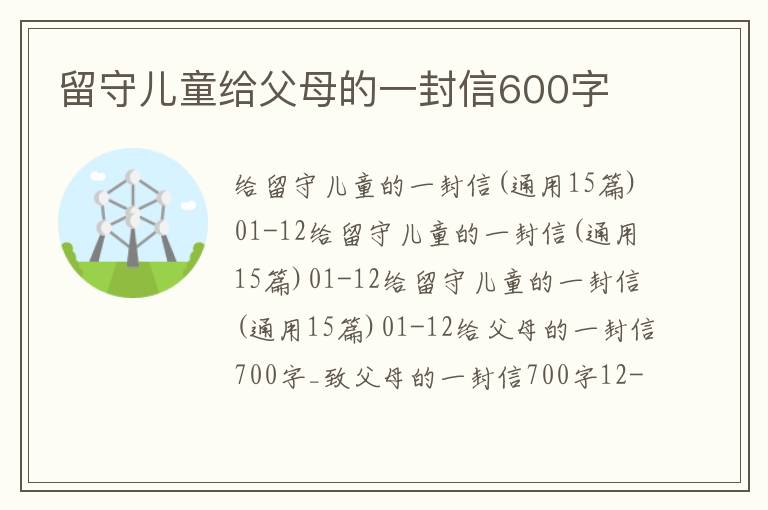家书的力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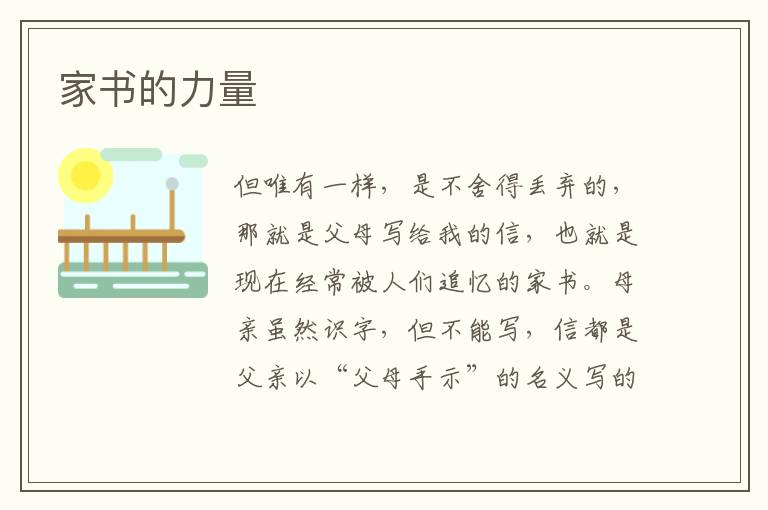
在天津生活了将近40年,大大小小搬过十来次家。每次搬家,都要丢弃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。但唯有一样,是不舍得丢弃的,那就是父母写给我的信,也就是现在经常被人们追忆的家书。
38年前,我刚16岁,第一次离家从河北农村来到天津工作。因为家中排行老小,以前也从未出过远门,所以父母不放心,便要求我每隔一个月左右就给家里写一封信。父母收到我的信后,再及时回信。母亲虽然识字,但不能写,信都是父亲以“父母手示”的名义写的。起初,父母的信都写得很长,从吃饭穿衣到合理安排开支(那时我每月只有30多元的收入),从热爱工作、尊敬师傅到团结同事,可以说事无巨细。几乎每一封信,父母都要嘱咐我保重身体。有一次,我在信中流露出想家的心思,父母便在信中鼓励我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,同时也经常告诉我家中一切都好,不用惦记;有时还把侄子、外甥顽皮、淘气的事情告诉我,排解我的寂寞和孤独;有时得知我在工作、学习中取得了一点成绩,也会来信鼓励,并提醒我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。
1983年,我考上了大学,父母便经常在信中过问我的学习情况,每一学期的成绩,都要求我如实汇报。有一次,为了听一位名人讲座,我和许多同学旷了课,老师大为恼火,凡是那天未到的期末考试全部记为60分。父亲见到这门课的成绩,很不满意,在信中让我说明原因。从此,我再也不敢旷课。娶妻生子后,父母对我放心了许多,关心点也从学业转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和孩子的教育。当得知我为了补贴家用需要到外面大量讲课时,父母很是担心。有一次回老家,父母看到孩子挑食,特意给我们写信要让孩子改掉这个毛病,以免影响发育。
1995年之后,父母和我们家中都装上了电话,方便了很多,父母的信就越写越少了。有时我给父母写信,父亲通常会来电话说:“信收到了,咱全家都好,就不给你回信了。”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,觉得不如看信那样印象深刻,而且信是可以反复看的,打电话却什么也留不下。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写于2008年10月11日,那是在收到我给他买的《资治通鉴》之后。当时父亲来电话时,我正在吃饭,信号不好。父亲说:“你先吃饭,我给你写封信吧。”就在写完信的当天晚上,父亲心脏病发作,紧急送往医院,不幸于10月1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那封信是我回家奔丧后发现的,信封已经写好了,这也成为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。
父母写给我的信,共有200多封,其中既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名言警句,都是看上去很普通的话语,但这些话语却饱含着对我的关爱、教诲和引导。回想起来,自己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顿下来,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可以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,与父母信中的叮嘱密不可分。在父母的信中,我汲取到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,懂得了自尊自爱、自立自强。